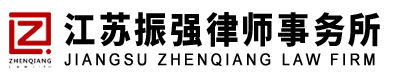【振强说法】引诱、欺骗所得供述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 作者:肖田
“讲讲清楚,让你取保。”
“没什么事情的,我们要处理的是**,不是你,你讲清楚,什么事情都没有的。”
“你讲清楚了,我帮你向法院打招呼,给你轻判。”
……
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讯问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上述语言,这些引诱、欺骗性质的讯问方式,对于由此所得口供的合法性,有无影响?可否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抑或可认为是讯问技巧或者侦查策略,从而得出上述瑕疵不足以否定其合法性的判断?
一、从实然法角度看
带着上述疑问,笔者梳理了与刑事案件证据有关的我国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
1、《刑诉法》;
2、《刑诉法解释》;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5、《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
6、《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7、《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8、《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9、《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10、《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上述文件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最新现行版本)
笔者注意到,上述文件,至多对引诱、欺骗的取证手段做了形式上的禁止性宣示,但未规定罚则,即如果违反了,如何循一定程序实现实体保障?比如说程序性制裁。
这种禁止性宣示,最为经典的表述方式是刑诉法(2018年修订)的第52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同时,上述所有的规范性文件中,在明确可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列举中,都没有将“引诱、欺骗”手段纳入其中。
也就是说,从实然法的角度看,“引诱、欺骗”的手段,虽被我国刑事法明确为“非法”,但是由此非法的“毒树之果”所得到的证据-供述,其法律地位并不明确。
二、从司法实践看
以无讼案例为工具,输入关键词“引诱、欺骗”,除去以“引诱、欺骗他人吸毒”为罪名的案例,以时间的先后为序,笔者梳理了排名前100的判决作为研究样本。
该100份判决书中,辩护人或被告人均提出受侦查机关“引诱、欺骗”才作出了最初的有罪供述,而无一例外地,该辩解均被法院以“经审查,与事实不符”、“经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调查,经本院庭审审查,认为侦查过程中不存在引诱、欺骗等违法行为”、“供述均系侦查机关通过法定讯问程序取得,其供述内容稳定,且与其他相互佐证,足见其供述内容客观真实”、“辩称侦查人员引诱、欺骗而供述犯罪事实的辩解,无证据证实,而在案证据讯问录像亦证实侦查人员并无引诱、欺骗言行”、“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实不存在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行为”等理由驳回,部分判决甚至对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此种辩解不予理会,迳行判决。
因此,从判例情况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希望以“引诱、欺骗”来排除供述的证据能力,难度极大,而法院倾向于不要求侦查机关自证清白。
三、从学界观点来看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认为,实际上我国刑事立法关于“引诱、欺骗”取证手段的规定是有缺陷的:一方面明确宣示其违法性,另外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模糊化处理,同时还明确规定秘密侦查的合法性。这样会造成司法认识上的矛盾,实践中的困惑:既然“引诱、欺骗”取证被禁止,为何秘密侦查合法?为何不像对待“刑讯逼供”可进行非法证据排除一样,对待同样也属于非法的“引诱、欺骗”所取得的口供?因此他建议:“可以在刑诉法中从反面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情节严重,严重侵犯司法公正、严重侵犯公民人权的应当予以排除’”。①
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认为,“法律不应该严禁在犯罪侦查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但是应该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那些以恶劣的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②何教授的观点和陈教授的观点是类似的。
四川大学龙宗智教授的观点:我国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以‘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为核心要件”。③基于此,笔者学习后理解:考虑由“引诱、欺骗”手段获取的口供是否需要排除,要以 “痛苦规则”这一实质标准作为判断依据。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李勇(悄悄法律人)的观点是:对于引诱、欺骗所获得的证据并非一律排除,需要具体分析。原因在于:一、一般的引诱、欺骗手段并不侵害当事人基本的权利,没有达到严重危害人权的程度;二、基于诱导、欺骗所供述的是事实的反映,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三、侦查实践中很难区分讯问、侦查策略和诱供、骗供之间的区别;四、刑事程序法制发达的国家对于“引诱、欺骗”手段获取的供述也并非一概排除。他还进一步指出,具体分析的主要依据是以下两个因素:一、引诱、欺骗的程度。当该程度严重到使得相对人感受到痛苦,且已经影响到其自由选择供与不供、说与不说的意志,而不得不供述、陈述时,由此得到的言辞证据应予排除。反之,则无须排除。二、所得言辞证据的真实性。通过经验法则或者其他证据的印证来综合考察,如果引诱和欺骗所获得的言辞证据不客观真实,当然应予排除。④
笔者在学习时感到,其实李勇先生提到的第二点,重点也许可以不放在考察证据资格的问题上,而是放在证明力问题上。因为不具真实性,该证据没有证明力,无论其有没有证据资格,其结果是一样的。这个认识或许在我国刑诉法对于“引诱、欺骗”手段所取得证据的证据资格进行模糊化处理的现实语境下更为务实。
如能修法,使之更为完善,当然是极好的。但站在当下,着眼实然法现状,其对于“引诱、欺骗”手段获取的供述,虽然宣示了其非法性,但并未设置排除规则,如何对待“引诱、欺骗”所得的言辞证据?这个问题始终都在,且已不容忽视。笔者认同上述学界大咖的观点,认为相关口供是否需要排除,一方面考虑引诱、欺骗的程度。具体可参照司法实践中,排除刑讯逼供所获取供述时依据的“痛苦规则”:痛苦达到足以左右相对人意志时,其供述应予排除;反之则不排除。另一方面,可以综合经验法则和其他证据,来全面衡量所得言辞证据的真实性: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也与其他证据相左,不具真实性的,予以排除;反之则不排除。
管见,求教。
①详见《欺骗取证:问题之源与立法取舍之争》,由秦莹整理,载于检察日报,2012年2月27日第003版。
②同上。
③详见《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龙宗智著,载于《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2期,第77页,转载自《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第16-24页。
④详见《刑事证据审查三步法则》,李勇著,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33-141页。

肖田,男,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著名法律平台“无讼”作者、“律赢惠”作者,中共党员,十年公安派出所、刑侦、经侦、法制、特警等多办案部门从业经历,数次立功授奖,发表文章若干。致力于用简单、生活化、形象的方式说明复杂、枯燥、深奥的法律问题,寻求最快、最短、最高效路径解决法律难题,工作语言英语可选,多从事企业家及个人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企业及个人刑民商跨界法律事务、刑事案件代理。